七十六年前的8月15日,臺灣的放送局與朝鮮、日本同步播送了日本天皇在前一日深夜親口錄製的《終戰詔書》。
臺灣的命運自此轉了個大彎,早已停頓的唱片工業再也沒有復甦的可能,而原先的音樂風格來不及謝幕,就已下臺。

純純演唱的〈雨夜花〉。
1937年之後,臺灣的唱片發行數量開始如雪崩般快速下滑,從一年七百多面跌到1940年僅剩106面,剩下9個唱片品牌殘存於市面上。
或許是大膽,或許是對市場的樂觀,也或許單純就是熱愛音樂,已經以〈白牡丹〉一曲流芳肆布的音樂人陳秋霖,在國家總動員法實施的1938年,推出東亞(後更名為帝蓄)唱片,成了戰前臺灣最後一個成立的唱片公司。主要的歌手月鶯生不逢時,縱令嗓音可比秀鑾,卻無從一展身手。另一位歌手兼創作者吳成家在戰後也很活躍,但他此時寫出的〈港邊惜別〉、〈甚麼號做愛〉、〈阮不知啦!〉才是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。
1941年後,市場上唯一的「新唱片」只有一套古倫美亞唱片合輯「臺灣的音樂」,內容是從該公司曾經出版過的各樂種代表作,是故嚴格來說,日治時期的最後幾年並無新作上市。
換言之,從1926年才算是有計畫、連續出版各類曲盤的唱片工業,到了1940年代就氣數已盡,這樣短暫的唱片歷史發展從全世界的音樂史看來,是極為特殊的。撇開戰後初期唱片出版混亂又荒雜的狀況,單單聆聽流行音樂的風格,國民政府遷臺後的臺語歌曲與戰前的唱片比較起來,兩者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。比如,文夏最早灌錄的一系列78轉唱片中,翻唱了戰前歌曲如〈河邊春夢〉,和戰前的音樂風格有著明顯的差異。
終戰前後音樂的斷裂性,指出了歷史的激變,以及感官與品味的劇烈差異,是重寫臺灣音樂史時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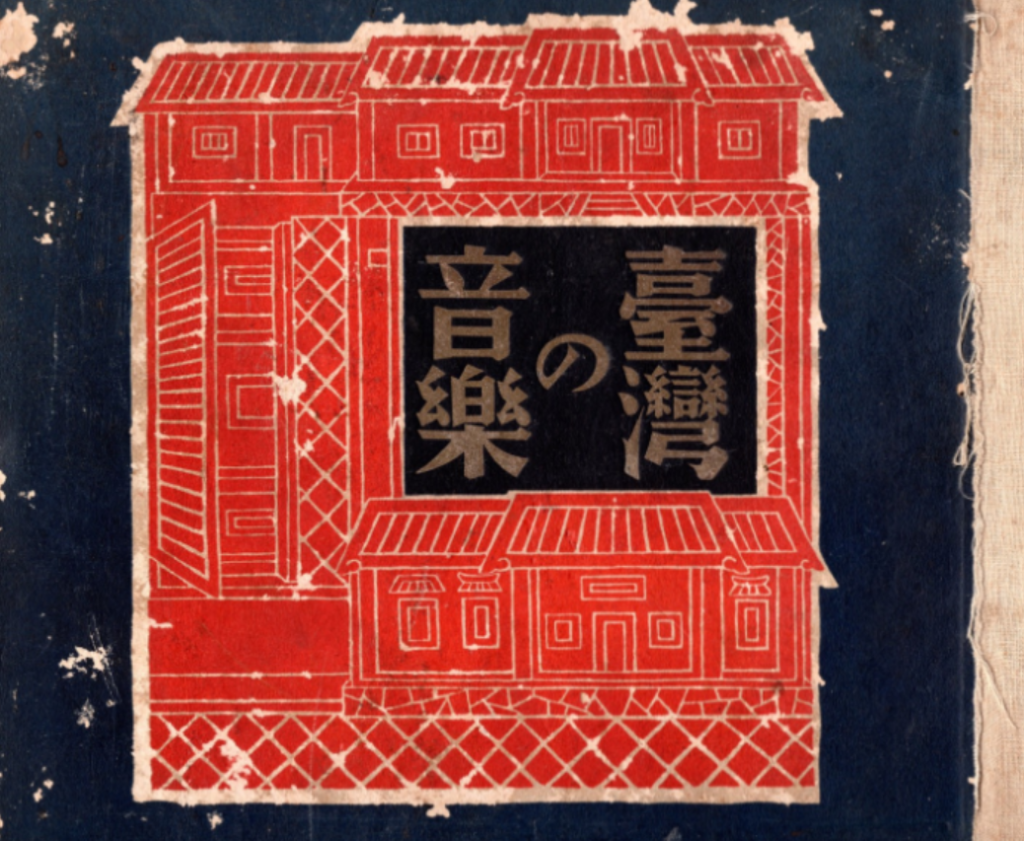
最後再回來說說廣播上的終戰。
這個消息要到在玉音放送的第二天,才在臺灣當時唯一的報紙《臺灣新報》上刊出。
可能你會好奇,為什麼沒有在一般比較熟悉的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大報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上刊出?原來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早已在1944年4月1日停刊,廣播節目表最後出現在3月30日,且只剩下零星節目斷斷續續在一天中播出。
實際上,就算到擁有收音機的人數不斷增加,直到1942年,約13.4%的在臺日本人擁有收音機,然而臺灣人只有千分之7.7。因此,是收聽玉音放送而非經由他人轉述才得知消息的臺灣人,很可能比想像中的人數更少。
此外,究竟除了天皇講話之外,臺灣民眾當天聽到的廣播還傳遞了哪些消息,後人已經很難拼湊出全貌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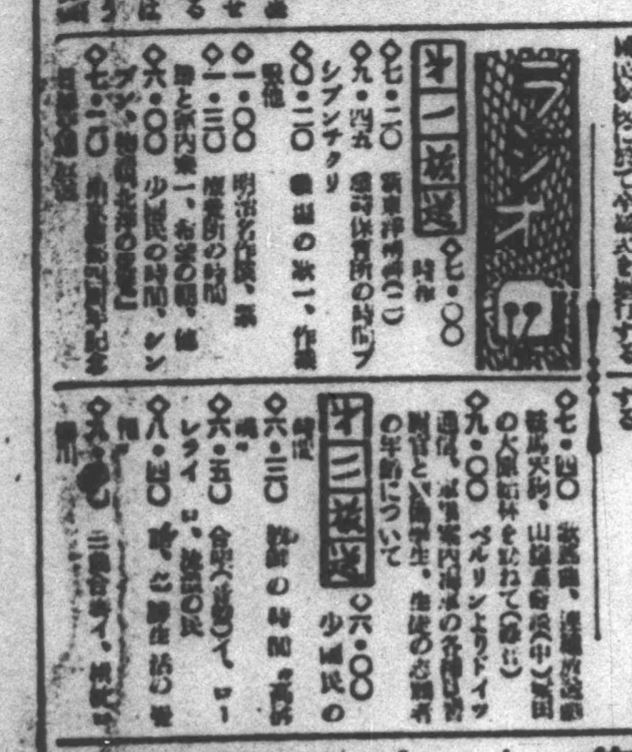
參考資料:
林太崴,《從圓標資料看戰前臺灣唱片品牌與產業發展》,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,2019
洪芳怡,《曲盤開出一蕊花:戰前臺灣流行音樂讀本》,臺北:遠流,2020
何義麟,〈日本戰敗與玉音放送〉,《臺灣學通訊》第86期,2015年2月,頁24至25
呂紹理,〈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(1928-1945)〉,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第19期,2002年5月,頁297至332